摘要 7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,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,部署下半年經濟工作。通稿里,有一個表述引起了島叔的注意——緊緊抓住處置“僵尸企業”這個牛鼻子,更多運用市場機制實現優勝劣汰。說這話...
7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,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,部署下半年經濟工作。通稿里,有一個表述引起了島叔的注意——緊緊抓住處置“僵尸企業”這個牛鼻子,更多運用市場機制實現優勝劣汰。說這話的背景,是要深入推進供給側改革,推進“三去一降一補”。也就是說,去杠桿、去產能、去庫存、降成本、補短板的五大經濟任務,處置僵尸企業是“牛鼻子”——這個比喻,可以看作是首要切入點,也是影響全局的關鍵節點。
如果聯系7月中旬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的話,習近平的表述則是,“把國有企業降杠桿作為重中之重,抓好處置’僵尸企業’工作”。
處置僵尸企業,我們都聽過。但對處置僵尸企業有如此高度的定位,這就有意思了。
數字
簡單來說,“僵尸企業”,是指長期入不敷出,依靠財政或銀行“輸血”才能維持生存的企業。
這樣的企業有多少呢?去年國資委摸底梳理出,中央企業需要專項處置和治理的“僵尸企業”和特困企業2041戶,涉及資產3萬億元。另外,2016年中國人民大學在《中國僵尸企業研究報告》中指出,電力、熱力、冶金、石油加工等行業中僵尸企業的比例較高,其中,鋼鐵的比例是51.43%、房地產為44.53%、建筑裝飾31.76%。
報告還指出,從所有制來看,國有和集體企業中“僵尸企業”的比例最高,遠高于民營企業、港澳臺及外商企業中的比例。可見,“把國有企業降杠桿作為重中之重”就顯得尤為重要。
為什么長期入不敷出,卻依然不市場出清,還要留著、甚至銀行還要繼續給予輸血呢?
依賴
答案也不復雜。
從行業分布看,“僵尸企業”主要分布于鋼鐵、煤炭、電力、冶金、石油加工等傳統經濟部門和產能過剩行業。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三十年間,這些行業為城市化進程、基礎設施建設輸送了源源不斷的“鋼筋水泥”“鐵公機”,為中央和地方政府貢獻了可觀的利稅,也解決了大量的就業、承擔了社會保障功能;中國也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。
事實上,每一輪危機后,傳統部門都會被當做經濟的“穩定器”。特別是在國際金融危機后,外需沖擊、出口急劇下降,以“四萬億”為代表的投資計劃,和配套的貨幣寬松,傳統投資這駕“馬車”讓中國經濟增速V型反轉。但“藥方”過猛,帶來了“一放就亂”、盲目上產能、大量舉債等后遺癥,拖慢了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步伐。
現在大家則看得更明確,目前土地、勞動力等要素價格越來越高,資源、環境的約束越來越緊;這種市場條件下,“僵尸企業”自我造血能力更顯得不足,只能依靠財政補貼、貸款、資本市場融資或舉債來“輸血”。
中央之所以如此看重處置僵尸企業,是因為其中蘊藏的風險。
風險
2016年3月,首例地方國企違約事件——東北特鋼違約事件爆發。該國企2015年第一期8億短期融資債券違約,到了7月,已有連續7只債券違約;10月,東北特鋼進入破產重組程序。
這不僅揭開了地方國企困境的冰山一角,還讓債務違約的陰云開始籠罩在投資人心頭。隨后,山東、山西、內蒙古、安徽等多個地區的國企債務償還出現風險,甚至是危機。“區域性風險”,說的就是這一類。
雖然有風險,但在銀、政、企特殊的關系中,地方政府傾向于通過行政手段來呵護“僵尸企業”,掩蓋了債務風險。例如去年5月,河南省出臺舉措要求“建立抽貸、壓貸提前告知制度,對正常還本付息、并且整體授信條件沒有發生變化的企業,各銀行原則上不抽貸、壓貸或通過要求增加授信條件而變相不續貸。” 河南一些煤炭、電解鋁、鋼鐵企業便保住了信貸規模不壓減。
處置風險,要降杠桿。
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,僵尸企業的平均資產負債率是72%,一般企業的平均資產負債率是51%。比如鋼鐵行業,中鋼協2016年會員的平均負債率為69.6%,負債率低的都是規模小的企業,11家大型企業則負債率超過90%。
國家資產負債表研究中心數據顯示,2016年,實體部門杠桿率高達227%;2015年,我國實體部門的利息支出是GDP增量的2倍,2016年為1.4倍——也就是說,我國的經濟的債務償還壓力巨大。
另外一個數據也引人注目:2016年,我國政府債務負擔占GDP比重已經達到55.6%。非金融企業債務中,又有70%左右是國企和地方融資平臺債務;而國企中,則包含大量產能過剩行業,如煤炭、鋼鐵、有色、化工等。如何化解這樣的債務負擔,將是對很多地方管理者的嚴峻考驗。
咋整
毫無疑問,處置“僵尸企業”是個龐雜的系統性工程,其中有幾個關鍵的問題:人往哪里去,錢從何處來,債務怎么銷。
習近平曾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強調,要做好轉崗就業、再就業培訓等各項工作,發揮好社會保障和生活救助的托底作用。要區別不同情況,積極探討有效的債務處置方式,有效防范道德風險。
人社部部長尹蔚民今年3月則表示,化解過剩產能,安置好分流的職工,是一個關鍵性的工作。2016年化解鋼鐵煤炭過剩產能,涉及到了28個省份1905家企業,安置了72.6萬人,今年化解過剩產能大約需要安置職工50萬人。
回顧歷史上的幾輪國改,80年代國企改革,從計劃模式走向自主經營、自負盈虧的道路;90年代末,國企通過并購重組、債轉股,以及下崗分流、減員增效等措施,提升了綜合實力,走向了國際舞臺。
處置“僵尸企業”不能一刀切,造成“一收就死”的現象。對于暫時遇到經營困難但在管理、品牌、技術上有一定競爭力和成長性的企業,可以通過兼并重組、混合所有制改革,讓企業重煥活力;
而對于連續虧損、不符合結構調整、轉型升級的“僵尸企業”,正如《人民日報》權威人士談話中曾指出的,“那些確實無法救的企業,該關閉的就堅決關閉,該破產的要依法破產,不要動輒搞’債轉股’,不要搞’拉郎配’式重組。”
從這個意義上看,我們或許可以理解為什么把處理僵尸企業作為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、經濟任務的“牛鼻子”看待了——
第一,處置“僵尸企業”,并購重組促進產能去化,提升集中度,有利于實現供給側改革。以寶鋼武鋼為代表的央企合并看,既淘汰過剩產能也強化龍頭優勢,加速周期性行業的出清,而真正符合“轉換動能”要求的,戰略性新興產業將獲得更好的發展空間;
第二,處置國企“僵尸企業”有利于金融資源在國營部門和民間部門均衡分配,服務實體經濟的金融效率將更高。過去“僵尸企業”的過度吸血,對民營企業融資造成“擠出效應”,而民間部門在經營效率和創造就業方面具有一定的優勢;
第三,有利于防化金融系統性風險。對國企“僵尸企業”主動去杠桿,市場化方式優勝劣汰,可以理順政企關系,糾正要素價格的扭曲。同時,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,打破各級政府的剛性兌付,遏制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負擔,實現規范舉債融資。打破剛兌還有一個好處,就是促成整個社會無風險利率的下行,降低實體融資成本。
前陣子,《人民日報》在防金融風險的文章中提到,既要防“黑天鵝”,也要防“灰犀牛”,引發市場廣泛討論。“僵尸企業”、地方債務,某種意義上也可以看作是其中一類:
灰犀牛生長于非洲草原,體型笨重、反應遲緩,你能看見它在遠處,卻毫不在意,一旦它向你狂奔而來,憨直的路線、爆發性的攻擊力定會讓你猝不及防,直接被撲倒在地!所以危險并不都來源于突如其來的災難、或者太過微小的問題,更多只是因為我們長久地視而不見。


 手機資訊
手機資訊 官方微信
官方微信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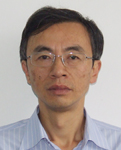

 豫公網安備41019702003604號
豫公網安備41019702003604號